
时间:2023/1/1 19:02:54 来源:新文网
分享到微信朋友圈
历史兴味、人文关怀与“重庆路径”——读王雨中短篇小说集《十八梯》
作者:杨不寒

作家王雨在小说领域的多年深耕,让他的写作在地方上越发重要,在全国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以重庆移民三部曲《填四川》《开埠》《碑》为代表的一些长篇小说,都自觉地用一种历史与美学相结合的方法写作而成,其中既有对本土历史文化的持续发掘,更有对地方乃至整个人类所表现出的真诚关怀。新近,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十八梯》,和王雨此前的创作有着一以贯之处,同样灌注着一种较为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热衷于在具体的社会历史中去发现故事,并且在行文中始终流露着一种人文关怀。集子共有《十八梯》《产房》《船神》等15部中短篇小说,多数已经在《新华文摘》《小说界》《红岩》《长江文艺》《四川文学》《滇池》等刊物上发表,《产房》《十八梯》等小说还被改编成了电影。在某种意义上,小说集《十八梯》早在出版之前,就已然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可。我们相信,作为一个整体的小说集《十八梯》,能更全面地反映出作家王雨的面貌,因此它有着被进一步做整体观照和讨论的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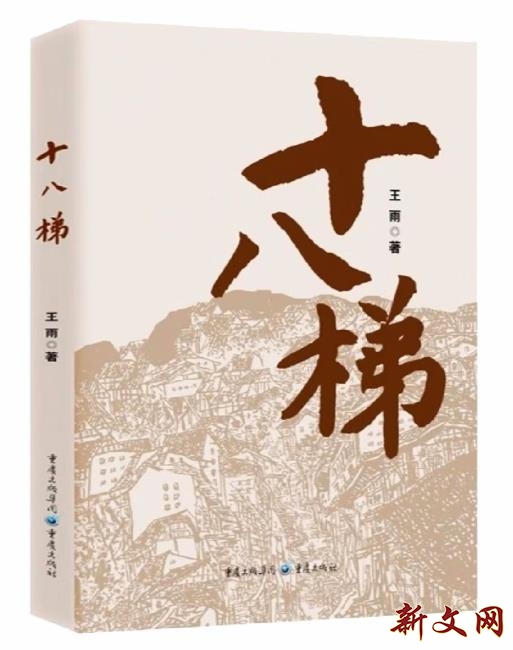
一
《十八梯》的结集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偶然性,它并非是先有一个主题后才进行的系列创作,也并不是专门收录的某一题材文本的合集。不过,就像上文所说的那样,小说集比较一致地显现出了现实主义倾向,这种一致性倒很好地反映出了王雨创作的特点。如果我们要分析这种特点的构成,迎面而来的首先便是王雨下笔时洞悉历史的深远目光。小说集《十八梯》中写重庆古迹十八梯与生活在其中的人的今昔之变的《十八梯》、记述抗战时期宜昌大撤退的《船神》、歌颂江姐等革命先烈的《江水悠悠》、呈现卢作孚创业艰辛的《一波三折》、赞美汶川大地震中人类展示出的伟大情谊的《生死不离》、反应激进年代中个体命运之波折与情感之坚贞的《源》以及状写在政治与战争波澜中弃暗投明的国民党军人的《回头者》等绝大多数文本,都是可以视为历史小说。
就算在纪录桂阿姨坚韧一生的《桂阿姨》与反应医护人员在新冠疫情中可歌可泣的奉献的《等待明天站起》等文本中,作者也显现出了一种不拘泥于个体生命,而把个体放在时代中来看待的历史眼光。应该说,小说都是时间的艺术,是对一段有长度的时间的模仿。但《十八梯》集子内的小说所面对的那些时间,却都是某些历史进程中最惊心动魄的时刻,与广大人民群众息息相关。这让集内小说因有别于一般的、日常的和个人的叙述。它们虽然篇幅短,但其历史意蕴却是深厚的,它们是吉光片羽,但却分明是一个个大时代与大事件的裂片。譬如《桂阿姨》一文,主要记载了桂阿姨为“我”的成长与幼儿园的经营而呕心沥血的一生,但其背后却勾连解放战争、反右倾扩大化与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事件,往往唤起人们的集体记忆。
作者的这种历史意识,让集内小说显得颇具中国传统小说的本色。中国文学历来有两大传统,一为诗骚,一为史传。后者对小说的发生有不可忽略的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小说的一大滥觞——司马迁的《史记》中就多有小说的笔法。在这种渊源下,长期以来,人们评价小说时便常以其类于史传为高妙。此外,在小说尚被视为文学之末流的年代里,人们只好以其有史的价值来为其正名。譬如,《四库全书总目》中称《因话录》“虽体近小说,而往往足与史传相参”,其中就透露出了古人对小说与史传的态度。小说可以为史之补一论,固然忽视了小说本身的价值所在,但也足以映射历史与小说之间的微妙联系。这是因为中国人历来看重历史,创作者与接受者往往有着无意识的历史兴味。这与西方人对普鲁斯特式个人记忆的一度沉醉有所不同。王雨以及他的这部《十八梯》所显示出来的历史性味亦是浓厚的,不少篇章反应的一些重大社会事件,甚至可以补证历史。
作为医学教授的王雨,自有一把他的切入重大社会事件的手术刀。这也让他对很多重大事件的关注点变得与众不同并且专业可信。譬如一般人对汶川大地震的关注都停留在受灾者的层面,想起此次灾难脑海中只得断壁残垣的景象,对救灾医护人员所经历的辛劳、遭遇的危险缺乏认识,《生死不离》《等待明天站起》等小说的笔触就深入到了白衣天使的群体之中。除此之外,王雨对重庆地方史的长期关注也自然而然渗透到了他的创作中,让他写出了很多不为人熟知的历史事件。罗广斌等人合著的长篇小说《红岩》对江姐入狱前经历的书写尚为有限,《江水悠悠》则描写了江姐入狱前的人生轨迹。可以说,小说集中绝大多数文本,不但呼应了中国文学的史传传统,也让小说集满纸皆是历史的烟尘,读来波澜壮阔,令人思绪深远。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忘记克罗齐在面对历史时给我们的警告,对官方记载下来的正史要始终保持警惕。或许,恰恰是小说集《十八梯》对历史题材饶有兴味,也是一种“应然律”的想象中,为沦为档案材料的历史塑造了活色生香的形体。在历史小说的光谱上,《十八梯》集子的价值不只在于“为史之补”,更在于它“史”的书写中努力实现着“诗”的自由,并且赋予了历史以有血有肉的真实性。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要理解历史就必须从“人”的立场、角度和感受出发,否则我们获得的就仅仅只是冰冷的概念。作者擅长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中寻求故事发生的空间,尽量还原历史现场,给文本以真实感和厚重感。在这个精心挑选的空间里,作者或用小人物的遭遇来折射历史潮流,或用英雄人物的行动来梳理重大事件的始末。就像黑格尔要求的那样,“诗艺要找出一个情节或事件,一个民族的代表人物或一个接触的历史人物的核心和意义”,[1]作者的讲述并不是简单地罗列数据与材料,而是紧扣着故事的主题来凸显人物的性格,甚至是人物的情绪和感受。且不说《回头者》以宁孝原的个体遭遇为聚焦点来回望重庆解放,也不说用《船神》以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的行迹来反映宜昌大撤退,单就看《鹤》一文,画家伍鶷的人生经历又何尝不处处都是来自“历史”的巨大影子呢。伍鶷在重庆大轰炸中出生,在阶级斗争中家道中落。当代中国历次社会政治运动,从抽象之物,变成了他身上真实可见的东西。此外,在《源》《大山的回鸣》中,特属那个时代的背景,更是被消融到了人物坎坷波折的命运中,成为“水中盐,蜜中花”[2]式的存在。文中没有对激进年代里某些荒谬行为的直接控诉,但秦福根、姚雯丽、水箐、赵敏等人的悲剧性的人生依然让人唏嘘不已……正因这种种以人物映射历史而非以历史来驱动人物的笔法,《十八梯》集子中的文本便比一般的历史记载更加血肉丰满,气韵生动,不但让人觉得可信,还因为真实而具备了感人至深的艺术冲击力。
二
对重庆历史文化的津津乐道,让小说集富有了历史兴味,但王雨并没有忘记要用艺术的心灵来消化那些材料与故事,使其成为了审美对象,成为小说。单纯模仿或者说再现历史并不能创造美,毕竟真正意义上的美总是心灵的表现。《十八梯》小说集所具备的感人力量正来自于作者在塑造人物与叙述故事时,字里行间的情感灌注。王雨注意到了历史海浪对人命运的深刻影响甚至改变,但他也明白对于个体生命来讲最真实的并不是“时代”“历史”“阶级”“人民”这些大词,而是他/她在具体生活中所感受到的喜怒哀乐苦辣酸甜。他既意识到那些“海啸山崩”的巨大威力,但在与笔下人物相对面时,他更关注的却是“海啸山崩”如何进入人们的生活,人们又如何在紧要关头做出艰难的选择,他们又如何应对这种选择带来的后果。就这样,王雨把他作为一个作家的人文关怀,灌注到了叙事之中,使得小说集中重要的不再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中的人们,以及人们怎样在狂澜中保持良知与尊严。
首先,王雨在小说中为英雄人物献出了讴歌。一九三八年十月,侵华日军占领武汉后继续西犯,兵锋直指宜昌。作为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民生公司总经理的卢作孚,临危受命,主持宜昌大撤退。这一场艰难的“战役”,经过重重考验后终被攻克。小说《船神》正是以卢作孚冒着危险**到宜昌考察的过程为主线,还原了这场“中国版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具体情景。小说以紧促笔调烘托紧张氛围,成功塑造了一个果敢勇毅、务实肯干、为国为民的卢作孚形象。小说最后,撤退任务完成,卢作孚也乘船返回重庆,路过大撤退时领江兼船长的孙正明的遇难处时,作者写道:
轮船缓缓驶过孙正明等人遇难的长江水段,卢作孚目视高天厚土大山急流默默祭奠,耳边响着哒哒的枪声和呐喊声。他迎风挺立船头,似一尊浩气凛然的峡江石。
作者意图塑造的硬朗形象,如同雕塑一般,在这里完成了最后的錾刻。在《江水悠悠》《一波三折》乃至《回头者》中,都可以仰视到英雄人物光辉的形象。但并不是站在光中的才算英雄。对日常生活中或者平凡岗位上那些表现出优秀品质的人,作者也欣赏有加。《源》中货车司机秦福根被姚雯丽抛弃后又被红卫兵殴伤下体,多年以后终于解开心结,并且发现自己的养子竟然就是当初和姚雯丽结合后孕育出的亲生儿子。三人间应该说恩怨重重,但在相逢时却冰释了一切。对于荒谬时代赠予的命运他们毫无怨言,反而在对命运的勇敢承担中显示出了可贵的坚韧品格和良善本心。至于《鹤》中的画家伍鶷,面对曲折的人生他总是保持乐观;《产房》中的护士长肖春,繁琐且压力重重的工作也没有消耗她的爱心和母性;《等待明天站起》中的穆毅,中年遇到爱情,正筹备着走入婚姻殿堂,可当疫情来临时,他与女朋友却义无反顾地奔赴了抗疫前线……这些平凡的身影在《十八梯》集子中都因为本身的积极、友善但不可被命运驯服而变得不再平凡。他们在危险与苦难前彰显出的人格尊严与人性光辉,是他们成为了“凡人英雄”。
与赞美英雄相呼应的,是对弱者的同情和对行差踏错之人的谅解。《产房》的故事是怎样发生的?杜英产后因羊水栓塞而死。丈夫李泉在职业医闹者的诱导下找医院麻烦。护士长肖春成为了他讨伐的重要对象。李泉是一个货车司机,脾气暴躁而心思单纯。在生死、医院、医闹面前,无权无势的他都算是一个弱者。尽管他充满愤怒地做出了一些无理取闹的事情,但作者每每写到他时,笔调都是深沉的,其背后正在一份同情之理解。又比如《源》中的姚雯丽,她有过不负责任的青春往事,生下孩子后又将其抛弃。但作者并没有单纯地谴责她,而是为她的行为找到了历史性的理由。多年以后姚雯丽和儿子的相认,不但证明了她本心的善良,还反映出了作者对人性本善的笃信。米兰·昆德拉认为:“认识,是小说唯一的道德。”[3]作者面对负面人物时的推心置腹,让小说认识到了一般意义的历史书写所忽略的事。小说也在这里找到了自己存在的理由。总之,有人住高楼,自然就有人一身锈。对后一类人的关注,可以看作《十八梯》集子的另一重人文关怀。
但作者并不是一个不会愤怒的人。小说集中的讽刺和批判虽然不多,但往往切中恳切,发人深省。集内最具讽刺意味的首推《红绿灯》。小说写的是某医学教授小区门口的红绿灯失修,而这里又车水马龙,过马路便成为了冒险。人物的行动因此开始了:他处处寻求解决红绿灯问题的门径,但却像是寻求进入城堡的K一样处处碰壁不得其法。故事最后,坏了的红绿灯终于通过政协提案的方式得到重视并被修好,教授正高兴,却又发现了另一处失修的红绿灯。像这样具有讽刺蕴含的还有《丹顶鹤》。这既是一个动物寓言,也是对人类侵害大自然行为的一次文学批判。此外,作者还惯于在行文中偶尔逸出,夹带着批评社会问题。比如《产房》便讽刺了邮政局大厅工作人员的尸位素餐,《一波三折》在赞颂主人公卢作孚的爱国忧民和雄才大略时,也对宋子文等庸俗官僚和国家蛀虫暗加批评。
整个小说集的色调是明朗的,作者向往美好未来的心灵充满了正能量。他笔下的人物少有颓废气息,情节或许曲折但结局大都指向于光明。那怕在粗暴的历史潮流和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前,作者也总是坚持着他积极乐观的笔调。《江水悠悠》《船神》等反映革命历史的小说自不待言,《十八梯》《源》等书写个体命运的小说也为主人公安排了喜剧结局。《生死不离》《等待明天站起》等小说可以纳入新世纪以来灾难文学的范畴,故事中的人们总是用爱来抗拒着灾难……等等一切,其中蕴藏着的正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对苦难人间的真切关怀。
三
除却《丹顶鹤》这篇科幻动画小说外,《十八梯》集子所写历史,所写日常生活,所写人们的情感、性格和行动,都是和重庆这块热土息息相关的。优秀的作家总是拥有属于他自己的文学地理,譬如鲁迅的鲁镇、张爱玲的上海、沈从文的湘西、李劼人的四川等等,不一而足。所谓文学地理,它的形貌总处于作家的想象与建构之中。它们也是作家创作的一种路径。作家试图走向某个文学中心,乃至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总要通过某一特殊的地方路径。正是无数条地方路径,最终编织起了整个中国的文学版图。地方路径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专门术语,但借用来讨论王雨这样专注于书写地方并且开始走向全国以至海外的作家,想必也是相宜的。
作为地方路径的重庆,在《十八梯》集子中,首先是一座英雄之城,有着荣耀的红色革命历史文化。小说集中的《船神》《江水悠悠》《回头者》《一波三折》等文,突出写到了重庆三峡发生的“宜昌大撤退”,重庆陪都时期全体军民与日寇空军间的较量,以及地下革命志士与特务们的血泪斗争等与重庆革命历史相关的重要事件。作者在小说中,对当年的政府建制、政局战事、民间传言、重庆街道等史料信手拈来,轻而易举就真实地搭建起了叙事背景。他们很多都可以看作是典型人物:《江水悠悠》中的江竹君(被捕后化名江竹筠)是解放战争时期重庆地下工作者的典型、《回头者》宁孝原是重庆解放前夕国弃暗投明的民党军官的典型、《一波三折》中的卢作孚是上世纪四十年代腐败官僚体系下民营企业家的典型。这些人的身份、地位、学养和社会经历各有不同,因此他们都有着自己特别的精神面貌。但他们的性格却有着相似的一面,那就是重庆人的率性耿介、泼辣豪爽。为了凸显这种“重庆性格”,小说中的人物对白大都使用重庆方言。总之,他们既是“那一个个”,同时也是“那一群”。而这样一群角色所构成的小说集,反过来又为重庆红色革命历史书写增添了新的一笔。
诚然,就在这些以重庆革命历史为主题的小说里,作者也总每每写到重庆的日常生活。小说集《十八梯》虽然常常选择宏大的历史事件作为书写对象,但它却依然充满生活的烟火气。一个地方的性格特点,总是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小说集中的故事,或被放置在山城古道中,或是被放置在大都市的背景下。种种重庆生活,既具有辨识度,又让读者在真实中看见感情与温度。《回头者》开篇写主角宁孝原与赵宇生的相约,便让事件发生在茶馆中。作者浓墨重彩写到了茶馆文化,使得一股浓郁的重庆气息扑面而来,让人瞬间意识到即将发生的是一个“重庆故事”。而在另一些非描写重大历史事件的篇章里,烟火气息就更重了。同样写重庆人吃茶的就有《鹤》,这是一篇逆时序叙事的小说。按照热奈特的观点,我们可以说《鹤》中故事时况就是画家伍鶷的大半生,其叙事文时况就是叙事者与伍鶷喝茶并回忆往事的那个下午。一壶龙井功夫茶从小说开始喝到结尾,真有重庆人黄葛树下摆龙门阵的滋味,而作者还不忘在小说开篇处提醒读者:“山城沱茶也可以,清香养胃。”《十八梯》集子中的重庆日常生活元素就更多了。且不说十八梯本身,太平门水码头、南山古木、老君洞、吊脚楼等等地方性物质文化也遍布字里行间,其中承载着重庆人日复一日的生活印记。而《产房》中的洪崖洞吊脚楼,吸纳三教九流的人物,更是重庆人的一个小江湖。至于医院产房门外那棵高大的黄葛树,始终陪伴着也见证产房中的故事,就像重庆其它地方茂盛生长的黄葛树,在岁月里默默陪伴着也见证重庆人的生活一样。
小说集《十八梯》中的重庆是中国的重庆,也是世界的重庆。作者在小说中建构重庆形象时,并不孤立的谈论重庆,而是视野开阔地将其视为中国的一个部分来进行书写。《等待明天站起》既是灾难小说,也可以看作爱情小说。它讲述的就是新冠疫情时医护人员间的爱情故事。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分别是重庆人与武汉人,这场灾难表面上延宕了他们的婚姻,实际上却加固了两人的爱情。从地方路径来看,作者在《等待明天站起》中立足于重庆,通过灾难书写把重庆与武汉联系在了一起。重庆受到了疫情影响,但积极配合国家疫情防控的号召,还派出了支援武汉的医护队伍。重庆在与武汉这座城市以及蔓延至全国的疫情的接触中,显现出热情开放而舍生忘死的自我来。作为中国有机组成部分的重庆形象由此彰显。从另一个层面看,小说集《十八梯》中的重庆还是世界的重庆。中国早已融入世界发展的浩荡潮流中。重庆直辖市作为中国后起的时尚之城,自然也是一扇面向世界的窗口。《一波三折》中的卢作孚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已经走出国门,去往美国、加拿大等地购买商船。时间来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小说《红绿灯》也通过国外专家的眼睛,来展现或者说衬托出重庆的发展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十八梯》中的画家明月在文革时期出走海外,如今归来重新在十八梯开办书画店,借重某种世界级参照物,暗示出重庆的今非昔比。
小说集《十八梯》中的重庆是发展着的重庆。王雨倾心于讲述具有较长时间跨度的故事,这就意味着具有历史意识的他必然要注意到时代迁改对故事背景所产生的影响。他的人生经验是丰富的,对重庆历史是熟稔的。从抗战时期《船神》中的“宜昌大撤退”到《候鸟生活》中当代人飞往海南过冬的“候鸟生活”,重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都可以在小说集内找到痕迹。《桂阿姨》中的时间跨度长达七十年,用幼儿园的变迁折射出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短篇小说《十八梯》更是写重庆向现代化猛进的一个典型。故事里,为了更好地打造重庆旅游文化,十八梯经历了修旧还旧地维护整改。而这种维护整改,恰恰是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一环。小说通过对十八梯现代化进程的书写,让重庆经验与整个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经验相呼应,不但打破了小说的地域性,还使其成为了当今时代的真实见证。
总之,小说集《十八梯》注重挖掘重庆本土最典型的文化内涵——红色革命历史文化,以此确立了重庆的基本形象。在这个基础上,作者并没有忘记小说应有的地气,以对日常生活的描写为其赋予了生动的血肉。重庆人爱热生活的一面也在其中展现了出来。集内小说在谈论重庆时并不局限于自我,反而能够把重庆本土文化放在全国甚至全国的视野下进行观察,并且将其融入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之中,从而让重庆成为了中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十八梯》中建构的重庆形象有两个相辅相成的内涵:一是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重庆;二是与外界有着密切关联的重庆,以及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大道上重要一员的重庆。通过这样的叙事策略,重庆在整个中国文学版图上不可或缺。重庆的社会历史就是中国的社会历史,重庆人的喜怒哀乐就是所有人的喜怒哀乐。重庆不仅仅是中国的局部,而成为了一个不可替代的“中国”。从地方走向中心、从民族走向世界,应该是每一个有抱负的作家的毕生追求。王雨的《十八梯》小说集在其中开辟出的路径,正是所谓“重庆路径”。这不但为重庆作家给出启发,也为其它地方的作家提供了参阅。
四
整体看来,深厚的历史意味,对人物处境和品行的善意关怀,再加上“地方路径”视野下的重庆文化元素,构成了《十八梯》集子的主要精神向度和审美内涵。也许是基于某种充满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理念,作者对现实世界也很少抱有怀疑。他在文本中常表现出对未来的乐观期许,遣词行文也磊落精当。尽管复杂与多义也是小说的品德之一,但在这方面,作者对读者却没有故意的挑战甚至冒犯。杨耀健在读过短篇小说《十八梯》后,认为该小说“可读性强,语言质朴流畅”。[4]小说集《十八梯》也是这样。我们在叙事层面,我们很难遇到障碍,阅读收获更多的来自于历史文化的吸收和真诚的情感体验上面。
王雨的长篇小说《填四川》曾参评茅盾文学奖,后来又被影视公司拍摄为32集电视剧。他的写作是勤奋的,“重庆移民三部曲”都是有分量有厚度的作品。应该说,王雨是重庆当代最值得期待的作家之一。单就新近出版的《十八梯》小说集来看,他所给出的“重庆路径”让他具备了基于地方又超越地方的广阔视野与文学前途。如果能够更精确地推敲语言文字,摒除一些个人化的作风,而让语言文字和理念水乳交融在一起,达到无迹可求不可凑泊的状态,那么王雨作品之风格想必能够更为圆熟,作者的独创性自会在人头攒动的当代文坛和浩浩荡荡的文学传统中,更为醒目的显现出来。
2022年9月
参考文献:
[1] [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 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47页。
[2]钱钟书:《谈艺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569页。
[3] [法]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第7页。
[4]杨耀健:《十八梯上的金色流年——评王雨短篇小说《十八梯》》,《文学报》。
杨不寒,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在读文学博士
审核:薛成毅